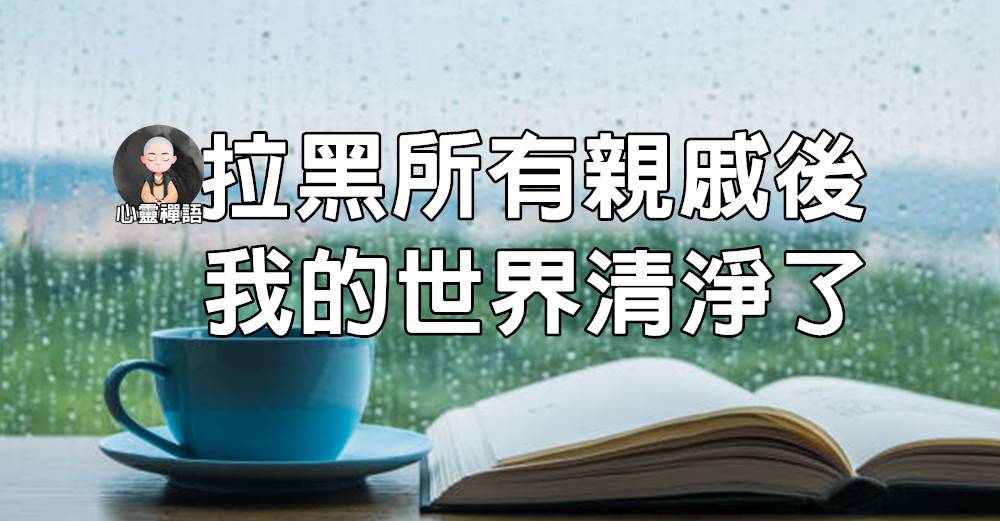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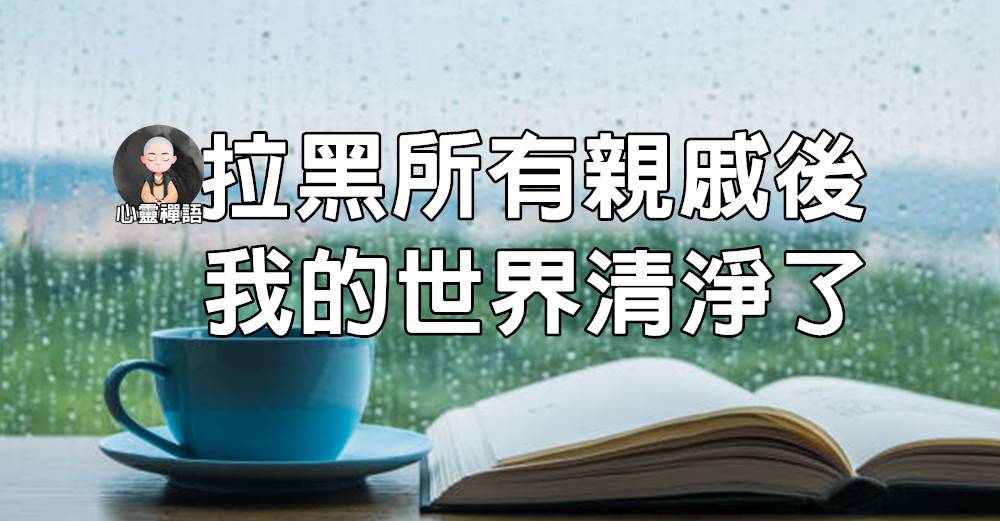


年輕人越來越不愛走親戚了。
親緣關係,父輩們維護得兢兢業業——花費時間、精力、財力,
甚至即便存在不愉快,也會顧念著「手足之情」而寬容忍讓。
年輕人對此卻嗤之以鼻。親戚們的盤問和攀比、
家族衝突中顯露出來的人性薄情和幽暗,都讓他們避之不及。
懶于、疏于、不屑于同二代以內的親戚互動和交往,社會學研究者將之稱為「斷親」。
2022年,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胡小武發表了一篇論文《青年「斷親」:何以發生?何去何從?》,
數據佐證了在90後、00後群體裡,「斷親」成為了一種社會常態。
利用寒假期間學生回鄉過年的時機,胡小武開展了隨機問卷調查,共回收了1200份有效樣本。
調查結果發現,年齡越小,與親戚聯繫越少。
18歲以下的被調查者「基本不怎麼與親戚聯繫」;
18~25歲、 26~30歲的90後年輕人大多數人只是「偶爾與親戚有聯繫」。

電視劇《父母愛情》劇照
家庭關係的代際衝突和矛盾,是引發這一代年輕人「斷親」的顯著因素之一。
在25歲高欣的眼裡,親人之間應有的分寸感和尊重,她從未感受過。
高欣的家在山東一個小村莊里,村里的房子不超過五十戶。
關係網的搭建全靠親緣,東邊幾十戶是一個姓,沾親帶故,常走動往來,
自己在西邊,幾十戶姓高的遠近親戚作鄰居,偶爾碰上面,也要叫個叔叔嬸嬸。
逢年過節一大家子要去爺爺家聚餐,因為自己家經濟條件更差,
父母常常被其他親戚打趣奚落,而他們總是選擇默默忍受,表面上還得送上笑臉。
更遠的親戚上門,宴席擺得大一些, 她和奶奶、媽媽、嬸嬸,
一眾女性只能在廚房吃飯,上不了桌。
爺爺奶奶重男輕女,過年時家裡的弟弟們都有紅包,只有她一個女孩沒有,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



















代表者: 土屋千冬
郵便番号:114-0001
住所:東京都北区東十条3丁目16番4号
資本金:2,000,000円
設立日:2023年03月07日
